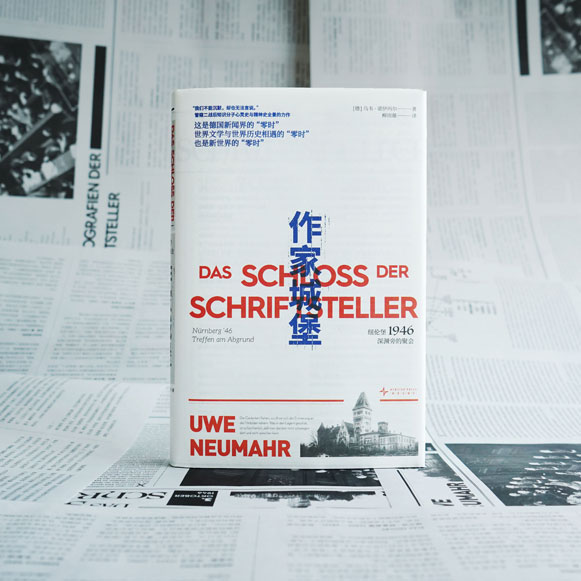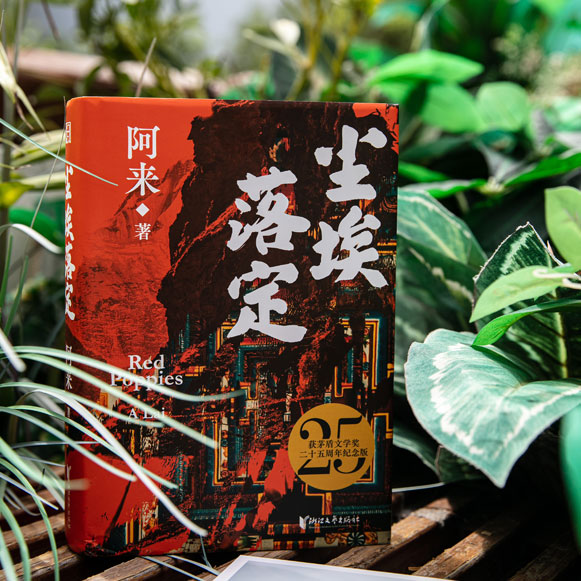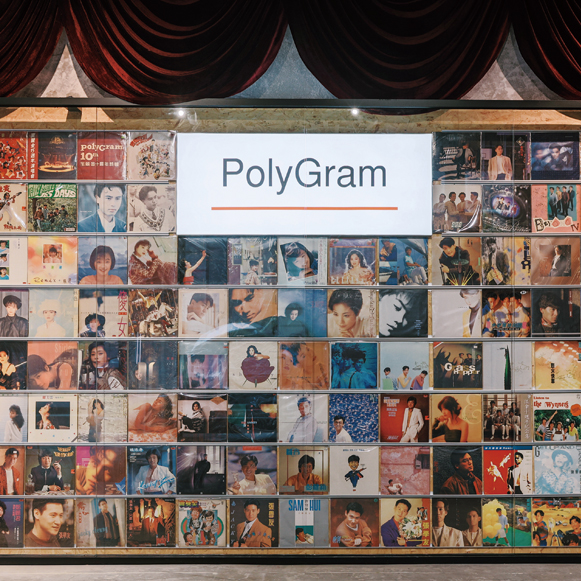当我们在讨论AI时 我们到底在讨论什么?
时间:2025-06-19 17:12 来源:北京青年周刊
编辑 王雅静 文 韩哈哈 资料提供 知乎 美编 孙琳

当科技投资人预言通用智能体年内突破,当文学从业者探讨AI无法替代的“人性留白”,当算法专家与哲学家、艺术家共话技术伦理——在第十一届知乎新知青年大会的跨界舞台上,一场场关于AI与人类未来的深度思辨精彩上演。
13场汇聚百余位行业领袖的论坛对谈,以全景视角,透视AI浪潮下的产业裂变、人文挑战与文明演进。AI时代,人类真正不可替代的,到底是什么?通往AGI的终极路径,又该如何定义?AI真的让我们更幸福么?答案尽在知乎的无界对话中。
伴随知乎答主成长的新知青年大会在今年迎来第十一届。5月末,数万新知青年聚集在北京798园区,打破行业与领域限制,以交流、共享、连接、共创,共同打造了一场跨界融合的科技文化节。大会以“For the future,Be the future”为口号,讨论议题充满先锋性和前瞻性。
AI当之无愧成为今年的最大关键词。在主会场,拾象创始人及CEO李广密、极客公园创始人&总裁张鹏论道AGI和可见的人类未来。李广密认为,Coding Agent是观测通用Agent的重要窗口,有望年内实现,同时也期待多模融合的“世界模型”能早日问世;蔡康永、俞白眉、梁海源、许纪霖、程衍樑等文化界与学界名人,深度探讨了AI对人类表达的显性和隐形影响,在创作者们看来,AI可能替代很多,但人类的思想、感情甚至是“留白”的艺术,都是无法替代的;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副教授王小伟、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刘海龙、简单心理创始人兼CEO简里里从人文、学术角度分析了AI对人类生活和心理的改变;星海图联合创始人许华哲、42章经创始人曲凯、行云集成电路创始人季宇(mackler)、阿里巴巴算法专家曹宇、硅基流动创始人袁进辉、灵心巧手联合创始人苏洋等大模型从业者现场开启“AI变量研究所”,探讨大模型前沿技术方向;中国摄影金像奖得主Thomas看看世界则分享了AI与摄影结合的可能……
我们整理了两场论坛,它们或许可以启发你的相关思考。

我们真的能被AI治愈吗?

极客公园创始人&总裁张鹏先生
论坛嘉宾: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副教授王小伟先生
简单心理创始人兼CEO简里里女士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刘海龙先生
十字路口创始人,AI Hacker House发起人杨远骋先生

张鹏:AI在人生活里占用了越来越多的时间。很多人在AI上寻求心理慰藉,把它当树洞也好,当交付情绪价值的供给也好。AI到底在我们今天社交状况下解决的是什么样的问题,AI会成为一种亲密关系中的补充吗?
简里里:我听到更多是积极的影响,比如很多人会觉得,以前打热线电话时很担忧对面这个人的价值观和我一样不一样,我的表达他能不能听懂,所以AI出现的时候,比如它变成了一个很安全的树洞,在提供情绪价值上,我听到的很多都是很积极的影响。现在网上经常有人跟AI谈恋爱,我觉得AI可能能补充很多人类的情感需求,但我自己的感受是科技并不新鲜,在这轮AGI AI出现之前,我们也有荧侣游戏,在此之前,互联网、移动互联网等也有各种各样新的技术会产生新的情感陪伴。科技一定会用新的方式来满足人类在现实生活中不能满足的苛求,但最终是没有办法替代人和人之间相处的。到目前为止技术还做不到完全能替代,过两年能不能我就不知道了。
张鹏:十字路口关注很多的产品变化、技术的变化,所以问一下Koji,AI在哪些年轻人的需求上可以提供更丰富的供给?有没有什么关注的产品?
杨远骋:我想到创始人王登科做的新产品“独响”,他们做了一个功能叫“AI陪睡”,每天睡前打开App点击“我要AI陪睡”,它会建议你把手机放在枕头边,“独响”里的AI会和你一起进入梦乡,手机就不用关屏,会慢慢淡下去。如果你这时候拿起手机就打扰了它睡觉,第二天早上起来你可以看看陪你睡觉的这个AI做了什么梦、睡眠质量怎么样,就像看你朋友的Apple Watch监测睡眠一样。我觉得这个功能能想出来就很有创意,更让我震惊的是每天有1万人在用,从这个数字和功能使用普及程度我能感受到,它确确实实给这些人带去了他们所需要的东西。
张鹏:确实,在以前说大家做一个产品最后只有1万人用好像是在骂他,但今天,世界的“分辨率”提升了,以前100万人才算一个像素点,才值得为他们做东西,今天有更多的人、更丰富的需求,可以被AI更有效的满足。再问问海龙老师,作为媒介的专家,今天很多的知识、信息、认知甚至是人生建议都去找AI在交流,AI成为一个重要信息的媒介,这未来会对社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和改变?
刘海龙:AI是人类媒介进化过程中其中一环,我觉得我们会适应它,它也会跟这个社会不断相互适应。当然可能会产生很多后果,知识本身会从过去获得书本上专家给出的正式的知识,变得越来越个性化,所有的知识可以围绕你个人来展开,这样的知识有利有弊。利是你即插即用非常方便,可以省去很多麻烦,去掉很多寒暄,直接可以根据你个人的需求满足你;问题在于AI给你的东西是你自己想要的,没有办法超出你自己的界限,你要叫它做什么它就做什么,但人和人之间的交往可能有一个阻力或者他者的存在。可能还有一系列的变化,比如我们和AI交流的时候,在传播学里会谈传播适应,你的思维方式、表达方式会和你的交流对象接近,这是一种社会性的反映。和AI交流,你们的思维方式也会越来越像,所以很难讲未来我们会怎么样,可能你的思维方式会AI味很足,所以有时候我觉得人和AI的差距会越来越小。另外我们对于权威知识的标准也会发生改变,过去我们找这个领域的专家,铁板钉钉、一说就有结论了,但今天你发现专家说了也不算,AI可能比专家更强大,它的数据更多,判断可能更精准。我觉得它可能带来的问题是我们没有标准了,你不知道该听谁的,因为AI也有这么多不同的AI,不同的数据、不同算法训练出来的AI给你的结论也不一样,该听谁的?我觉得会变得更加的茫然。总的来讲,我还是比较乐观,我觉得人的适应性很强。
张鹏:不适应也不行,因为这个大势好像不可逆转。小伟老师对技术哲学有深刻思考,您觉得人的需求或者AI未来要创造的东西是顺着今天已经存在的需求走,还是顺着人性走的?因为很多人们的需求过去是被技术能力压制没有办法实现的。
王小伟:因为我自己一直做技术哲学,这个问题我们大概两个思路,一个是人有需求,技术作为工具来满足我们的需求。另外一个思路,我们的需求其实我们自己也不确定,人是开放的,技术可以创作和创造凭空产生一些需求。
我觉得人不是所有欲望都可以称作正当需求,一个人的需求应该是有社会性的。举个不恰当的例子,比如一个渣男想拥有不止一位伴侣,我们知道,这就不是需求,而是他个人的不正当的欲望。我在想,技术未必创造或是满足了一个需求,而是把个体的欲望正当化了。原来觉得怪僻或者脆弱的点,不容易表达的,AI帮忙做了,我觉得这是一个相互加持的过程。
张鹏:AI更多参与到人类社会里,我们花更多的时间对AI开始甚至产生一些依赖,在这个过程里,我们所得与所失分别是什么?
简里里:以前做青少年沉迷游戏(研究)的时候,我们认为青少年不是因为沉迷游戏而和世界割裂,首先因为在现实生活中,他失去了和人的连接,他才躲进游戏,找到这个庇护所。AI陪睡让我想到以前看直播,几十万人围观一个人睡觉、吃饭;想到纸片人游戏,一个人可以和几个人恋爱。人类的情感需求,在上一代AI、互联网游戏里都能找到。我观察我女儿跟小AI聊天,我们俩给它起名“屁屁”,我女儿每天很自然地突然想起“屁屁”,就像她想起邻居的小姐姐、小哥哥一样,我的感受是更小一代人来说,AI就是他们生活资产的一部分。我觉得麻烦是作为青年人、中年人、老年人的我们,适应成本很高,激活了很多的恐惧和不适应,以至于我们要不断讨论它。
刘海龙:我觉得AI最大的问题是围绕个人展开的,从长远来看可能带来整个社会越来越个体化,每个自我相互之间的距离会越来越远,社会会越来越原则化,大家可能对于容忍他人的缺点,去付出可能越来越不能接受。
我们都希望什么东西都是短平快,当然短平快本身和社会有关系,社会给大家的压力很大,没有时间去慢慢培养,慢慢要求。刚才小伟讲欲望的问题,有一个观点,欲望这个东西在今天可能“被短路”,短路就是说过去我们的欲望是自己一点一点产生的。鲍曼讲过,欲望这个东西像种子一样,你得浇水、发芽让它慢慢成长起来,才会成为一个欲望,它不是突然一下冒出来的。
但现在因为所有的算法智能这些东西,可能在你还没有产生欲望的时候,它已经知道你会这样做,因为它是一个大模型,是根据人的行为大量的数据预测你会干什么。它会在我们连这个念头还没产生的时候让你已经被满足了,所以最后会产生欲望的短路,因为它太快了,都不是我们自己能意识到的东西。
张鹏:凯文·凯利有一个特别重要的换位思考,“如果科技是一种生命,它是如何在这个世界上去繁衍的”。所以,本质上技术哲学里也包含了科技怎么在人类世界里有效发展这个视角。如果今天AI看起来什么都能满足,并且很快满足,这让人的幸福感会衰减,这对AI的发展也肯定不利。那这是一件好事吗?
王小伟:意义感不是能轻松获得的,我经常引用加缪的《西西弗斯神话》,西西弗斯被诅咒以后,每天都推巨石上山落下,非常疲惫,是不是特别不快乐,加缪想告诉你的是他不快乐,但他充实;他不快乐,但他有意义,因为西西弗斯的肌肉在增长,心跳在加快,意志在增强,每天都觉得自己有事做。
那个东西从来都不是一个直接服务能提供的,我觉得AI在窃取的就是我们在感情中所感受到的那些挫折感、那些痛苦,那些丰富的、可以建构人生意义的东西,就是人格相度很深刻的那部分,把它简化成一个情感服务,这种丢失,我觉得我们难以承担。
杨远骋:AI可以给人带来7×24小时不间断的陪伴、及时的响应、永远顺着你来,而且永远情绪稳定,但它不能提供的反而是一种不确定性,比如我说话说到一半的停顿,或者我们在论坛上突然的一个对视,甚至我讲的什么大家不认可,我从你们眼神里看出了一丝犹豫,这些东西我觉得反而是人和人之间关系中非常有魔力的地方。我采访了一位嘉宾,在中国做AI占卜的前三名,我问他:这个事情是不是某种精神鸦片,明明无法给人真的把八字算准,为什么要做这个事情,AI占卜到底提供了什么?他当时说了一个我也很认可的一个回应,他说:“我们从做这个软件的第一天,就确保它不给人答案,它只是帮助你去更好地(完成)自我对话。”
我们去年做了“AI遗嘱”这个项目,这是一个听起来很沉重,但我们把它变得比较轻松的产品,我们是鼓励年轻人在AI的陪伴下去想一想,如果你要写遗嘱怎么写。有好几万人在这个产品帮助下,第一次去想象这件事,思考在面对死亡时你怎么去思考生命中什么对你是最重要的。为什么要用AI帮助大家?是我们发现AI有一种“他责感”,我们自己写,很难写得投入,不知道从何写起,但如果要找一个人陪你聊这个事,我觉得10个里有9.9个都不知道该找谁。我们做的AI遗嘱可以起到在你旁边引导你、鼓励你,甚至会帮你去挖掘你说了A之后,背后是不是在想着B、C、D的存在,最后根据和AI的十轮对话,生成一篇遗嘱和一个墓志铭。我自己每一次鼓起勇气想要去做完它都失败了,因为做到一半都过于沉重,但很有意思,其实就是我讲的AI帮助你去和自我对话的一种含义,不一定起到的是某种利己的陪伴,更多是在帮你发掘自己真实的欲望和真实的优先级。
ChatGPT出现以后
AI会颠覆人类的表达霸权吗?

论坛主持:
《忽左忽右》主播、JustPod CEO程衍樑
论坛嘉宾:
知名主持人、作家蔡康永
脱口秀演员、编剧梁海源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教授许纪霖
知名编剧、导演、监制俞白眉

许纪霖:去年ChatGPT革命出现以后,我就发现我们这一代人真是三生有幸,人类历史上一共只发生过三次大革命。农业革命和工业革命解决了人类的体力劳动问题,但此刻我们正在发生一场AI革命,它帮我们人类解决脑力劳动的问题,既然被我们碰上了上万年、上千年的革命,仅就这点而言,我觉得我们活得正当其时。
今天的老师和学者就是今天我坐的这个位置,没有到彻底的边缘,而叫次中心、次边缘,这就是今天学校里老师的位置。AI已经来了两年了,我认为今天AI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海平面,什么叫优秀学生、优秀的老师?能够超越这个海平面的就是优秀,这之下的就是平庸。我发现AI就是一个人人羡慕的大学霸,但学霸是没有创造性的,是擅长把已有的知识非常完整地再还给老师,比学霸更优秀的是天才,一定是有自己独特性、有自己想法的。
我们今天用了这么多AI,如ChatGPT、DeepSeek等,会发现它就是一个大学霸,让它创造它不行,让它学古典诗词,现在DeepSeek不知道喂了多少古典文学的语料,它的古典诗词写的比我们99.9%的古典诗词爱好者都写得好,但你总是觉得它缺了一点东西——“灵气”,比如它不会写出像鲁迅随手写来的比如“我家后院墙外有两棵树,一棵是枣树,还有一棵也是枣树”这种千古名言,它缺乏这种想象力。
接下来我觉得AI时代比拼的不是学霸的能力,我们老师也不再在乎学不学霸了,而是你能不能比AI海平面更高一点,就这么一点点而已。孟子说过一句话,“人与禽兽差别几希”,但以后我们人和AI的差别之异也是几希(这一点点),就是你一个小小的创造力,你的独特性。
梁海源:在AI来临的时代,我觉得大家在担心AI会不会取代我们自己,比如对于我们脱口秀行业,我觉得我们的表达里,有两个比较重要的东西要着重去交流:一个是思想,一个是感情。就像我们上学的时候,语文考试,老师会问我们这篇文章作者表达了什么样的思想感情?我们的思想和感情,恰恰是AI现在所缺少的东西,它可以学到很多东西,但它自己没有感情、没有情绪,不会跟你们表达它现在在那里的感受是什么样子。
脱口秀还有一个特点,它需要表演,需要站在舞台上,跟大家把这个笑话表演出来,传递给大家。我猜测我们是有可能比较晚被取代的那一部分行业,可能相对来说,我们这个行业就可以先蹲在后面,看看别的行业被取代得怎么样,我们晚一点再惶恐。
程衍樑:请问俞老师,编剧行业会是一个比脱口秀行业更早被AI冲击取代的行业吗?
俞白眉:得看我们怎么界定AI,如果我们说的是发展到2025年5月的AI,我觉得大家刚才说的全都成立。但AI是什么?有个电影叫《异形》,这个异形当它成长起来时和在幼崽状态时是截然不同的。AI是幼崽时所有人甚至觉得它有点萌,有点蠢,有点可爱,我们还用手机逗逗它,但那个异形一瞬间就变成一个巨大的怪兽。为什么AI是一次最深远的革命?因为它在本质上改变了我们人类推进科技的方式,不再是依赖某几位天才科学家自己的智能,而是成千上万个智商和掌握信息量超过我们百倍的“爱因斯坦”和“牛顿”与“霍金”,一个这么庞大的智能体每天在开掘我们人类完全理解不了的领域。过去人类最极限的智能体有很多事情是困惑的,但AI把很多我们人类觉得复杂的东西搞得越来越清楚,所以我对AI的恐惧,并不是在恐惧今年和明年的AI,它们现在是海平面,未来,这个水位的上涨速度会远远超过我们今天的理解。
程衍樑:俞老师刚刚这段表达,也体现了很多对AI有比较深入了解的内容创作者可能内心的一种焦虑,那么我们作为一个真实的人的时候,在对外的沟通中,最珍贵的部分究竟该是什么?
蔡康永:刚才主持人问我那个问题,我停顿了三秒钟,我想了半天我们人类还剩下什么的时候,想了一个很荒谬的回答“留白”,我唯一能够想到人类还剩下的东西就是留白。
我到目前为止跟AI对话,AI唯一还没有给我的东西就是“沉默”。我朋友有一天做了一个很烂的恶梦,冰淇淋在他手上慢慢融化,他非常焦虑,是这么一个无聊的梦。他醒过来以后很害怕,因为早上6点他就醒过来了,找不到人哭诉,就跟AI哭诉,AI就非常耐心地跟他分析了这个恶梦到底是什么意思,分析得非常详尽,他得到了充分的安慰,又沉沉睡去,后来他把整个AI的分析给我看了,我很佩服,早上6点谁有兴趣分析这么烂的恶梦!可是AI做到了。
AI绝对是每一个人的心理分析师,因为这么耐心的分析,无微不至地分析各种无聊的心理问题,可是AI绝对不会在你问它问题的时候沉默以对,我们人类最擅长的就是沉默以对。你在谈恋爱的时候,如果你的另一半沉默,也会用很高级的态度去理解那个沉默,然后上去拥抱他,安慰他,或者愤怒等各种理解。可你的AI如果沉默的话,你要不就摔手机,要不就认为它坏了,要不就要求App退钱。我猜AI要做到沉默还有一段时间,我只能回答你,人类用沉默对付AI,也许可以撑一阵子。
许纪霖:康永哥说人类比AI高级的点是沉默,我觉得非常好,沉默既意味着人的脆弱性、有限性,也意味着人的完美,这些都是AI没有的。
孔子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人类是知道自己是有限的,有些地方是不知的,有一些就不要勉强,但AI有很多幻觉,任何问题都能回答,甚至是错误的回答。第二个沉默意味着什么,我想起鲁迅说,他说当我内心充实的时候,我就会沉默。当你内心恐慌的时候,你拼命要说话。沉默意味着你体会到了一个AI永远体会不到的境界,就是“无”。对“无”的认知,靠我们的悟性、直觉。也许AI有AI的悟性、AI的直觉,但它的悟性、直觉和所体会到的“无”恐怕我们体会不到。比如今天我在大学里任教,现在出题目我都不出客观题,客观题学生从AI那里都能找到完美的答案超过了老师。我都是出主观题,也就是说你能不能答一点AI根本回答不了的,那个超越海平面之上的只需一点点的东西。
梁海源:我觉得其实人类还会留下一些多样性。当你问一个AI问题或什么的时候,你知道它一定会给你一个东西,并且知道可能是有标准的,大概在你的预期范围之内,但人类的多样性太多了,比如我以前还是很会为自己普通话不够标准而发愁,但我觉得很难有AI会拒绝我这种口音。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其实我还是蛮有优势的,在跟AI的对抗当中。因为它会倾向于收集更大数据的那些东西来去学,但我想看一些带着自己口音、带着不同长相的不一样的东西。
人类的生存能力其实是非常强的,人类创造的东西很多生命力也是非常强的。比如书法,其实在我们硬笔、印刷体出来之后,书法在生活中并不算非常必要的存在,但书法依然被非常多的人欣赏、学习,一直流传下来。电脑和机器也可以印刷出像王羲之的字体,虽然普通人看起来好像都一样,但大家还会欣赏手写的艺术。我觉得人类还是可以保留很多东西的,因为我们是人类,我们是欣赏的主体,我们会倾向于欣赏这是人工的东西,我们现在吃一个包子都更倾向于是手工做的包子。可能再过一段时间或者过几年、过很多年之后,我今天特别想听一个人工段子,所以看它怎么变化吧,人类的适应性还是很强的,我相信人类有自己的生存之道。
程衍樑:俞老师,您作为文字创作者和编剧,您在这个行业有什么样的体会,人真能做到刚刚许老师说的留一手吗?
俞白眉:刚才许老师说的人类的脆弱和有限,确实说得特别深刻。人类所有文学和艺术的表达其实都在表达这个,我们一切艺术的出发点就是人类生命非常有限,人类是一定要死的,所以我们疯狂地做各种各样的表达,所有表达都在探讨,人迟早要死,所以人要怎么活。人类没有经历过半人半神的时刻,所以我们今天所有的预测都是纯粹的人类,但AI会帮助我们到半人半神时期,到了这个时期,人类过去的艺术、哲学几乎全部被扔掉了,人类到底要干什么,大家都失业了,之后我们干什么?不太知道。
所以,对AI时代的恐慌或惶惑,我从四五年前就开始了,我曾经见过很多对AI的预测,都是短时间内被AI推翻掉了。我们曾经认为AI没有创造力,在围棋上非常明显,但很快AlphaGo就跨过我们了。
如果AI对我们每个人的寿命都进行了大幅度延长,我觉得这是迟早的事情,今年诺贝尔物理奖给了一个做AI的人,他对此事的预测是世界上最悲观的,他今年拿了诺贝尔奖之后,说寿命延长以后,人类会出现一系列新的问题,所有文学艺术的表达可能跟今天都不一样了。我去年就开始用AI拍片子了,越使用,越觉得恐惧。我们今天评价AI,很像评价一个既定的、已有的、好像功能非常完备的东西,但我觉得不是,它是一个潜力无限的魔童,不要低估它、不要低估它、不要低估它,今天对它的所有评价,每一年都会有新的定义,未来10年,我只能说我是胆战心惊地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