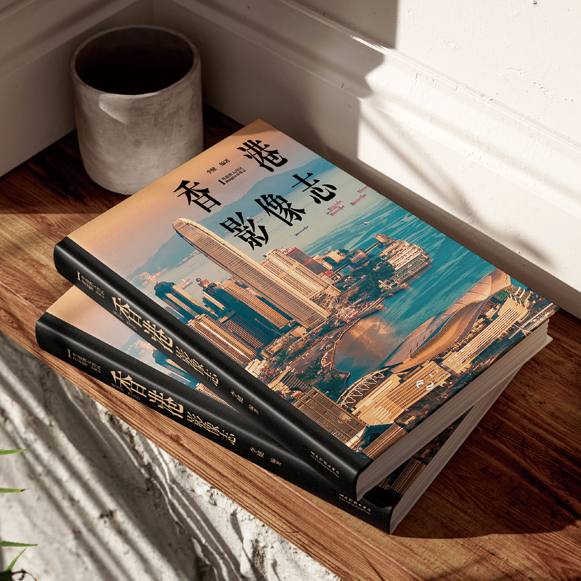“2024年古建行业杰出创新人才”张越 : 以如水之“韧” 赓续传统营造之魂
时间:2025-06-05 16:59 来源:北京青年周刊
编辑 曹宇 文 曹宇 摄影 解飞 美编 刘鹏

1940年,16岁的罗哲文考入中国营造学社,师从大家梁思成,从此踏进古建筑学之门,梁思成先生谆谆教诲、事无巨细,传承之间,为罗哲文打下一生受用不尽的基础;
若干年后,罗哲文获誉一代宗师,古建泰斗,马炳坚行拜师礼,成为罗门弟子。马炳坚同样是古建专家,其所著述的《中国古建筑木作营造技术》,被奉为业内圭臬,出版以降,加印超二十次;
及至马炳坚老师退休,沉甸甸的传承与责任交棒到张越手中——这位“古建所里的年轻人”“工作20年总说自己没出师的‘小学徒’”。
张越,现任首开集团所属北京市古代建筑设计研究所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经理,北京市老城保护房屋修缮修建技术专家委员会专家组组长。张越努力用中国传统建筑技艺修缮古建,同时探寻中国传统营造之法如何在当代焕发生机。2024年,张越获评“古建行业杰出创新人才”。
张越正式拜师并接手北京市古代建筑设计研究所所长时很年轻,四十出头。身份骤变,不仅使她成为古建界青年一代的中坚,也将她进一步带向传统建筑文化传承的前沿。
拜师礼上,马炳坚老师手书“上善若水,厚德载物”相赠。古建界往往以男性为主导,墨线斧凿总与刚健遒劲相连。而“上善若水”恰恰强调了“水利万物而不争”的韧性,木梁榫卯方寸之间,浸润出包容并蓄的传承新境。
梁思成先生、罗哲文先生、马炳坚先生,再到今天故事的主角张越,近百年匠心不辍、传承有序,只为留住残存于古建上的一抹历史余光。
古建修缮:先读懂这栋建筑的语言
宏恩观,始建于元,至今历七百载,位于北京钟楼北侧,紧邻中轴线,本刊记者与张越的对话,就在宏恩观大殿廊下展开。
所谓“大隐隐于市”,张越初到宏恩观修缮现场,这里正“灰头土脸”地隐在一条不起眼的小胡同里。观内场地解放后划归某国营工厂,上世纪90年代工厂迁出,宏恩观沦为杂院。后因钟楼前市场拆迁,生鲜肉蛋摊位也曾便宜行事在此“鸠占鹊巢”。
“大木构件开裂、槽朽、拔榫;墙体局部开裂、砖石构件缺失,屋面多处瓦件碎裂。”谈及宏恩观当年窘境,张越如在目前:“更重要的是几乎每块砖都‘说不清出身’,第一要务当然是测绘与记录。从屋面到结构,能留下来的必须保留,
不能留下的要替换成同质材料。”
上溯梁思成时代,直至当下,古建筑勘测唯人力艰辛方可为,并无第二法门。
“测绘”二字轻描淡写,背后真不是空调房里的画图与排版——无论寒暑登高爬梯乃为常态,往往是顶着学者、设计师的光环,身体力行野外生存者的日常。
这次“上房揭瓦”,张越带队揭开帝君殿屋面,意外发现椽子上方竟是薄石望板而非传统木望板,覆盖白灰背层,这是文献中极少记载的做法。为了复原,她与团队不断查阅古建案例,调配灰料比例,最终决定用同样的材料和方法重做屋面。“这部分结构外人看不到,但我们一定要做对。”张越坚持将工艺详细记录备案,为未来留下可考依据。
有趣的是,她把修缮比作“翻译”:不是用今天的语言替代历史,而是将历史原文忠实译给下一代。“你得先读懂这栋建筑的语言。”张越说:“我们做的事,就是帮它说话。”
帮文物说话,知易行难。张越特别强调“可识别性”:在修缮中添加的新构件、新材料,必须便于后辈识别。“比如一根檐柱,如果是现在的加装,就要在材质或颜色上做出轻微差异,哪怕只一道记录线。”她举例说:“不要掩盖‘加法’,而是告诉后人,这里我们动过手。”
张越认为,这是对未来修缮者最起码的尊重。
拂去“浓妆艳抹”:只因对文化敬畏
张越快人快语,结合一头利索短发,总之给人“短平快”的印象。她具备极强的“多任务处理能力”,采访的几个小时里,她似乎同时兼顾着几条“工作线”,电话不断、微信不断,竟然熟人也不断——鼓楼周边的老街坊、宏恩观文创商店的帅哥靓女等,三不五时地上来和“张所”招呼一番……看来她早已在这方土地“扎下根”。
忙归忙,跟她聊古建修复全没压力,张越总能深入浅出地把晦涩道理讲得活色生香自带画面。她说:“古建筑就像素颜美女,底子好。但年长日久,被层层叠加了诸多‘浓妆艳抹’。我们的工作,不是再添粉黛,而是卸妆,让‘她’露出真实模样。”
“卸妆”之比喻,在古建修复领域并不多见,但极为贴切。张越从不认为修缮是重建。相反,在她看来,修缮的本质是在尊重历史的基础上最大限度“留痕”,让古建在“今天”仍保持昨日的风采与气韵。
修缮宏恩观时,“卸妆”过程尤为复杂。张越介绍,当时的建筑后期作为厂房等使用,原貌早已淹没在后期建筑中:“我们走进现场时,几乎看不出原来的院落格局,它被密密麻麻的现代搭建物包裹严实。”更让人心疼的是彩画——原本庄严、精美的彩画被油漆遮盖,破坏严重。
“我们一层层剥掉后期涂料,只剩下淡淡的轮廓。”她说,这些原始痕迹虽不完整,却比“复制”的新彩画更有价值。在专家的指导下,特意清理保留了山门内侧构件上的彩画沥粉痕迹,让专家和公众可以直观对比原始与修复的不同。
“我们并非粉饰,我们是在还原。”张越强调。她用“美女卸妆”的比喻说服了甲方和施工方,最终选择了最少干预的方案。“古建修复,表面是技术活,本质是对文化的敬畏。”这种敬畏,不仅体现在张越的图纸上,也体现在她选择的每一块瓦、每一根梁、每一道工艺流程中。在北京历代帝王庙修缮过程中,同样在大殿外檐保留下了一间原始彩画的痕迹。
老城改造:修补人与人、人与历史的关系
从历史文化遗产修缮到老旧平房片区蝶变,北京城市更新的每一步,“城市复兴官”首开集团都深深参与其中。首开集团及下属各单位,积极探索城市更新路径,守护着北京的文化脉络和悠然古韵。
与历代帝王庙、宏恩观、故宫等身临其中恍若隔世的建筑相比,四合院更让张越感觉亲切。如今,张越与古建所同事们更成为胡同的常客。
“我们面对的不是一间房,而是生活。”张越提到一个令人动容的案例:在雨儿胡同25号院的改造过程中,居民被我们团队的设计服务工作所打动,在沟通方案时主动翻出老照片与团队分享院子的历史风貌——过去房屋什么样、门窗什么形式、影壁什么样……话里话外讲的是环境,但内核都是满满的生活记忆。
于是,张越与战友活跃在前门、西四、钟鼓楼前,她不仅是设计者,更是现场调研者、政策推动者和理念传播者。日常调研测绘练就了“铁腿”,也骑过电动、挤在平板儿车上,老旧片区房屋千变万化,往往状况百出,即便执行“分级分类、一院一策”的修缮策略,还是要靠“张越们”的一张“巧嘴”攻坚协调。
曾经有工作内容像她们一样的规划师发过一条朋友圈,这位年轻设计师以幽默的笔触记录了自己参与平房修缮的坎坷心路:“每天给居民宣讲、拆违建、沟通、博弈,最后不得不设计出四十八种窗户样式来满足所有住户的要求……”诚其所言,老旧片区城市更新工作就是要下足绣花的功夫,古建所投身其中,并不因为它简单,而是因为这项工作的艰难,因为这项工作两头连着政府与百姓。
如同绣花,张越特别强调通过细节打造“共生”理念。例如将原本私密的独门独院,通过功能划分与合理动线,改造为多户共享、互不干扰的空间。这种技术与人文兼顾的方案,避免了矛盾激化,在保留城市记忆的基础上,注入全新的生活理念。
“设计师不能把老城封起来,而是要让它活起来。”张越告诉记者。在改造前门、蓑衣胡同等片区时,她与居民反复沟通,寻找曾经在四合院居住多年的老居民座谈——“老城里生活的人,才是传统文化最好的载体”。
当然,这一切并不容易。例如某老旧片区的某三开间,前身是庙宇,大梁上官式彩画依稀可辨,历史信息丰富且木料并无腐朽,但房主一门心思打算翻盖重建。念及此事,张越不禁感慨:最大的挑战是要让大家意识到“修旧如初”,“旧”是传统,但“旧”不代表“破”。
修房是修心,对双方来说,都是。
上善若水的“韧性”
自梁思成先生一脉相传,张越的起点不低。尤其跟从恩师马炳坚(时任北京市古代建筑设计研究所所长),作为嫡传弟子一路培养20年。当年大学刚毕业,张越就一头扎进古建所,用她自己的话说:“开始五年都不敢抬头,唯有反复深读马老师那本《中国古建筑木作营造技术》。”
时光荏苒,“小学徒”已成为别人眼中的“张老师”,古建所目前有员工三十余位,其中设计人员十多位,张越也像师父带她那样培养年轻人:“我希望年轻人不只学技术,更要理解这个行业的文化逻辑。”
说回马炳坚老师手书相赠的“上善若水,厚德载物”八个字,张越在采访中多次提到自己的韧性,这性格恰与“水”呼应。韧性是积极的品质,很大程度上决定一个人在不同环境、条件下如何面对挑战,处理压力。
“出现问题时,人与人最大的区别就在于是否能够坚持。坚持的过程会伴随困惑或外来因素影响,压力之下,你能否坚定地完成这件事?能否顶住压力把它做好?这可能就是匠心,就是劳模精神之所在。”张越说道。

张越
首开集团所属北京市古代建筑设计研究所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经理
北京市老城保护房屋修缮修建技术专家委员会专家组组长
2024 年,张越获评“古建行业杰出创新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