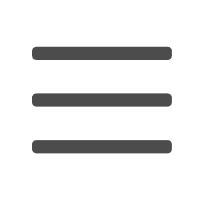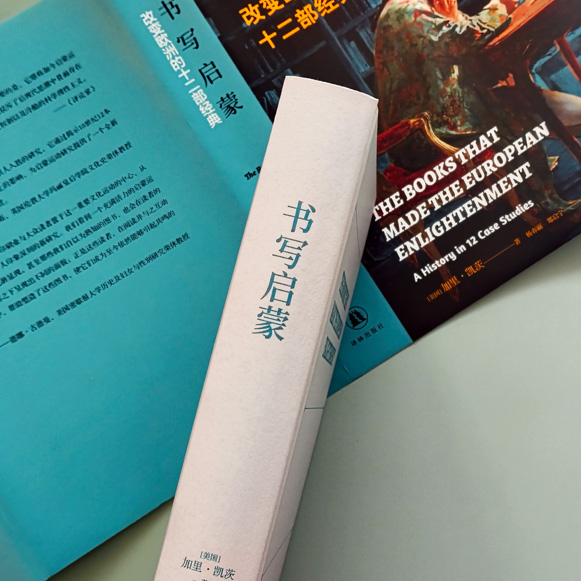收集时代的切片 重塑我们的观看之道
时间:2025-11-27 16:26 来源:北京青年周刊
编辑 康荦 文 张娜 图片提供 国际短片联展主办方 美编 聂琳
在过去八年的时间里,北京国际短片联展(BISFF)通过近500场展映、展览和公共活动展示了近1300部海内外作品。
作为中国最具有国际前瞻性和影响力的短片影展,他们摒弃赘饰和成见,力求以恰当、本真的方式呈现参展作品,让真正的才华与冒险得以无畏迸发。在不断发现前沿创作者和创作现象的同时,BISFF也在积极寻求作品同业内人士和热情公众的充分互动,试图达成一种作者、作品和公众的共同生长关系。

构建一个更庞大的生态系统
丁大卫于2017年创办北京国际短片联展(BISFF),其出发点是因为当时中国仍缺少一个具有BISFF这样特定定位的节展(九年后的今天仍是如此)。
北京国际短片联展(BISFF)的定位非常明确:更倾向于展示当代影像创作中最前沿的作品。这并非一个纯粹的产业电影节,也不仅仅是青年创作训练营,其真正关注的,是探索“影像”本身在今天意味着什么,它正在发生怎样的变化,以及图像媒介与人类的关系正经历何种扭转。丁大卫希望借此平台,将创作者最新、最实验性的作品呈现给大家。
“我们坚持了九年,做出了一些成绩,这本身就证明了其价值和生命力。虽然很难,但我相信前景是光明的。”丁大卫说,“我们并不想与产业衔接得过紧,但也不排斥它,而是保持一个合理的距离。事实上,从BISFF走出了不少后来成功拍摄商业长片的导演。我们希望构建一个更庞大的生态系统,让不同背景、不同诉求的人都能在这里找到位置,互通有无,进行交流。这种开放、不设壁垒的状态是最理想的。”

丁大卫
BISFF北京国际短片联展的发起人、总监对话丁大卫:
Q:你为何专注于“短片”?
A:我们对“短片”的界定很宽泛,规定竞赛单元影片在45分钟以内。
我选择专注于短片,是因为它是目前创作力最旺盛、可能性最丰富的体裁。尤其在当下经济环境下,我们这一代人怀抱着文化理想成长起来,却发现留给我们的创作空间非常狭小。过去那种按部就班、最终能获得资源拍摄长片的健康路径已经很难复制。未来,人们最有可能持续创作的,就是短片。
但这绝不等同于短视频。我们强调的是“短的艺术电影”或“电影艺术”,只是它的时长较短,但其艺术完成度和严肃性同样重要。
这个判断源于我作为影评人和电影节观察者的经验。如今,一个年轻导演完成一个长片项目,平均周期长达四年(从立项到完成)。人生没有多少个四年,而投入产出比却可能极低。在这种现实下,短片提供了一个更灵活、更可持续的创作出口。
Q:关于选片标准与趋势观察,你的切入点是怎样的?
A:对我而言,传统的电影媒介确实在衰退,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正因如此,短片和实验电影的重要性才愈发凸显。当过于光滑、同质化的消费型影像已无法提供不可替代的体验时,实验电影、档案电影(ArchivalFilm)的价值便显现出来。
因此,我们影展近年大量展示了记录、实验等方向的影片,也包括许多混合手法的创作,如引擎电影、伪纪录片,或融入大量档案材料的故事片。我们本质上是在探索:在影像创作上,人类的想象力和创造力还能抵达怎样的边界?
可以把BISFF理解为一个“时装秀”。大家来这里,是为了看到这个时代在影像上什么是重要的,今年的“颜色”和“剪裁”又是什么。
Q:是一个怎样的团队在做这些事情?
A:我们拥有一个专业的团队,光是选片人就有七八位。因为从节目体量上说,BISFF已是亚洲最大的短片电影节。要完成如此庞大的选片、联络和策划工作,需要足够的人手。我们整个核心团队仅15人,理论上支撑一个为期十天、超过百场活动的电影节,需要30人左右的团队。
我们的选片人都是专业人士,通过长年累月的工作,建立了广泛的网络。我们一方面通过与国际重要电影节(如鹿特丹、洛迦诺、法国真实电影节)保持同步,确保我们的视野和选片标准与国际接轨;另一方面,我们也会主动发掘那些可能被时代忽略的作品——有些片子可能在10年、20年前就已完成,但其重要性直到今天才被我们感知和激发出来。
Q:你们的观众群体是怎样的?
A:我们的活动确实吸引了大量文化从业者、专业人士和知识分子。但我们真诚欢迎所有人,我们的绝大多数放映甚至不售票,就是为了不设任何门槛。我们希望同时做好深度与广度:既要保证内容的前沿性与专业阈值,能满足顶尖学者复杂的美学探讨;也要作为一项公共活动,吸引非专业背景的观众,包括孩子和老人。我们有一位忠实的老观众,一位老太太,每年都会来。她告诉我,她平时在家带孙女,但就是特别喜欢我们的片子。这种反馈和唐宏峰教授认为我们的片子“非常深刻”的评价同样珍贵。保持这种宽广的受众阈值,正是我们一直努力的尝试。
Q:九年来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A:最大的变化首先是变得更成熟了。你不可能办了九年还在原地打转,整个运营的各个环节都更加专业、顺畅。
其次,规模显著扩大。第一届我们放映了100多部片子,当时已是中国最大的短片电影节。到大概2021年左右,我们已成为亚洲最大的短片电影节。
衡量一个电影节的关键指标,一是参展作品数量,二是首映率——尤其是全球首映的比例。在我们这里,98%的影片都是中国首映,其中10%-20%更是全球首映。这意味着我们是在与国际顶级电影节竞争并抢到这些片子的首映权。这得益于我们多年积累的声望和国际标准的专业操作,让创作者愿意将最重要的作品交给我们。
Q:关于“生态影像”的概念你是怎样理解的?
A:我们今年关注的“生态影像”概念,在国际上已活跃多年,但在中国却鲜有讨论。所以,表面上我们是在放映和策划,但实际上,我们是在一点一点地填补国内的诸多空白。许多重要的电影人作品,都是在BISFF完成其在中国乃至世界的首次放映。生态影像与环保主题当然相关,但它远不止于传统的环保纪录片或“人与自然”题材。它不是一个简单的议题标签——并非拍摄了动植物,就等同于生态影像。
我们更希望探讨的是更深层的维度:将电影的媒介性、时间性等本体思考,融入一个更广义的范畴中去讨论。我们选映的片子大多并非直白地探讨某个环保议题,而是引导观众去反思:电影创作本身如何对环境造成影响(即便是数码拍摄,其设备制造也涉及重金属污染等)?在人类充分反思自身与自然关系的基础上,我们该如何重新审视电影与自然的关系?我们将这个层面的思考纳入整体策划,在此基础上进行选片。

我们要像对待文本一样对待电影
“电影是需要不断被阅读和拆解的文本,而不仅仅是作为一种被我们感受的感官体验。电影是可以被切分被重组的,我们需要像对待文本一样去对待电影。”

朱塞佩·博卡西尼
活跃于德国与意大利之间的电影导演。毕业于博洛尼亚大学(DAMS,艺术、音乐与表演学系)电影理论专业,并于罗马奇内奇塔电影学院(NUCT Cinecitta)获得导演文凭。他的创作以研究为基础,专注于拾得影像、档案素材与实验电影的形式探索。
第9届北京国际短片联展呈现了意大利实验电影人朱塞佩·博卡西尼(GiuseppeBoccassini)在亚洲的首个作品回顾展。博卡西尼活跃于德国与意大利之间,同时自柏林FRACTO实验电影节2017年创办之初就担任影展艺术总监,其创作以研究为基础,专注于拾得影像、档案素材与实验影像的再组装与再书写。
博卡西尼的影像创作长年游走于电影史的废墟与感知的临界点之间,他以现成影像与档案材料为媒介,探索记忆、身体与观看之间持续震荡的张力。
在他的电影中,影像不仅被用来再现世界,更被用来审视影像自身的存在方式——它如何被拾起、被切割、被重新点燃。
对话朱塞佩·博卡西尼:
Q:我们的阅读和观影习惯变化很大,很多老电影在记忆中淡忘了。但昨天看你的电影,让我感觉“过去的人吃得都这么好”(指电影呈现的过去很精彩)。你似乎把老电影重新排列组合后呈现给我们。想请问你如何看待过去的电影?
A:我很喜欢老电影,因为它们与现在有相当的距离——在媒介、观众和作者之间都存在一种间隔。这种距离使它们的意图并非“征服”观众,而是更温和地存在。老电影多采用模拟信号(Analog),在整体表现上因此显得更柔和。
过去的观众对电影会有更多幻想和情感关联,而如今人们更多是“消费”电影。例如当年卢米埃尔的《火车进站》,观众会真的觉得火车冲过来,而现在的人对此类影像刺激已近乎麻木——过去的观众对媒介形式有更直接的反应,今天这种反应几乎消失了。我认为电影应回归过去的形式,重新寻找电影与观众、与其他事物之间的关系。人与机器的关系,就像人与动物的关系:人总想驯化机器,但机器其实有自己的主张和意识,并不完全受人支配。
Q:你觉得电影是有生命的?
A:不要把电影当成一个死的物质来看待,要把电影持续地作为一种现象学的经验来看待。我一直在做的事情是,如何让影像活起来。
电影可以一遍一遍地被播放,被反复观看,但是它在特定的时间与场地当中,还是拥有属于某一刻的唯一性。
这种活着的关系也是非常迷人的。
电影不仅仅是光线与镜头激活的一个平面,它更是记忆的载体。每一次拍摄与放映,都是与时间的一次互动。因此,电影将时间视若珍宝,也视为遗产——它如同翡翠,既是具有美感的物件,也是记忆的见证者,其中沉淀着无数时间的痕迹。这个比喻并非我本人原创,而是源自日本作家谷崎润一郎的文字。
此外,我也联想到另一个贴切的意象——尘埃。在中国文化中,尘埃同样富含深意。这位曾写道,在许多文化里,人们总试图拂去尘埃,但尘埃本身,其实也是记忆与时光的承载。这两个比喻或许最能传达我对电影的理解:电影是时光的见证,也是时间的容器。
Q:电影中多次出现钟表,是什么意象?
A:电影本质是关于时间与空间,或者说“空间中的时间”。时间线本身也是空间,如同时间自身的韵律和机械性,与电影内在节奏紧密相连。
将个人的情绪、情感与时间匹配串联起来很重要。很多美国电影关于赚钱、发财,时间自然也与致富的焦虑等主题相关。
每个人对时间的感受都不同:10分钟可能对某些人美丽而永恒,对另一些人却漫长难熬。在电影中,时间可以被操控,这种操控感让观众理解、保存甚至拓展时间。
时间也与生命岁月相关。计算时间,某种意义上是在计算自己的生命——这是非常西方中心的文化观念,即将人与生命置于宇宙中心去关注。但我认为今天我们也可以拓展时间:生命虽有限,却可通过某种方式延展时间,从而不做时间的奴隶。
我的电影中很多元素都可丈量时间,如火车、钟表、相机等科技产物。它们试图将人类像奴隶一样禁锢于时间观念中,而我想做的是打破这些机器,甚至打破这种时间控制。
Q:电影中有些重复的画面逗笑了观众,你期望观众有什么反应?如何看待这种“笑”?
A:我无法控制观众如何反应,也不想去设想或迎合他们的反应。重复对某些人可能有趣,对另一些人未必。我使用重复,是为了创造意义,而不只为逗笑。这有点像小孩子——我只是想创造一些有趣的片段,通过这些片段可以擦除事物原有的意义。但成年人总想建构某种结构,这是孩子不会做的。
我的电影更像作曲,如同创作音乐。重复是一种变奏、一种旋律,通过不断重复与变奏形成更大的乐章。
因此,比起让观众直接以笑或哭回应我更希望他们沉浸于电影的整体之中。但我不想让他们完全融入某种情境,所以有时会加入一些中断——不断震撼他们,推翻再重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