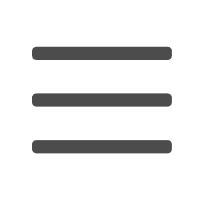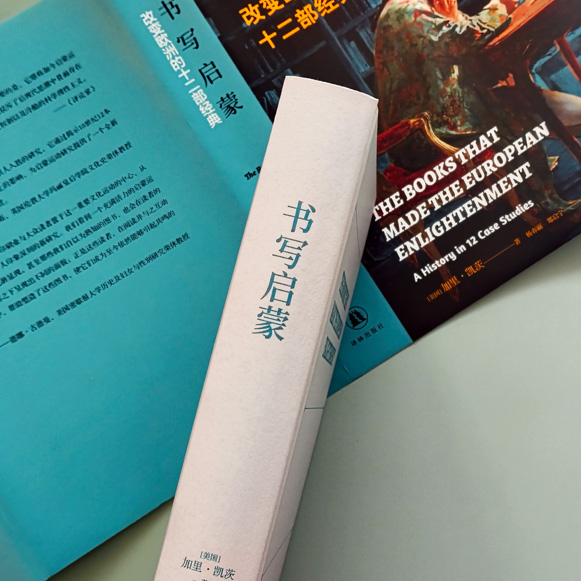一间女性的房间, 以及房间里的多重宇宙
时间:2025-11-06 15:02 来源:北京青年周刊
编辑 康荦 文 张娜 图片提供 受访者 美编 聂琳
在社会的土壤中生长,既依赖群体的滋养,又保有独特的形态。原来每株蘑菇都是立体的镜子,照见我们不敢示人的柔软与固执。我们俯身凝视大地的脉搏,同时也在端详另一种形态的自己。

吴文芳
与内在的自我温柔共生吴文芳个人作品展“与共WITHIN YOU”在北京沙滩北街3号院的“拾院”举行,古朴又现代的院子里面,长满了欣欣向荣的蘑菇。

吴文芳/文子|CINDY WU
一名独立设计师、软性材料艺术家。从小对艺术保有无限的好奇心,12岁开始进行专业绘画学习,擅长油画。同时,对于纤维艺术和原生态的材质以及制作技艺有相当丰富的经验。在艺术家的眼中,蘑菇不只是一类生物,更是一种观看世界的视角。它们生长在潮湿的、不被阳光直射的角落,安静,卑微,却从不放弃生长。像极了那些沉默的大多数——腼腆、平凡,在不起眼的位置,以自己的节奏默默扎根,从周遭汲取养分,慢慢向上延展。它们在成长中与自然建立联系,与土地、湿气、光线达成默契,从而获得一种安静而坚定的生命力。
蘑菇从不孤单地出现。它们成群而生,彼此依存,却又形态各异。有的伞盖饱满,有的茎秆纤长,有的颜色沉着,有的肌理斑驳——就像人间的我们,虽处在紧密的社群关系中,却依然保有独特的性格与样貌。当我们俯身靠近,仔细凝视每一株蘑菇,便能在它的轮廓与纹理里,照见自己的影子。
这场展览,并不意图让我们“拥有”什么,而是邀请我们学习“相处”。与蘑菇相处,也与自己相处。请慢下来,走近它们,问问自己:为什么是这一株吸引了我?它在对我说话吗?它映照出我内心的哪一片情绪,哪一种状态?
答案没有对错,感受不分高下。当你停在某一株蘑菇面前,感受到那种无声的牵引,那一刻,或许正是你与“最本来的自己”,一次温柔的相认。

对话吴文芳:
Q:这次以蘑菇为元素的创作,还是延续布料材质吗?
A:对,布料一直是我创作的主要媒介。但这两年,蘑菇逐渐成为我作品中非常主体的表达渠道。在蘑菇的世界里,我感觉自己处于一种相对自由的状态——创作没有太多限制,更像是一种自然流淌的过程。我所有的作品都是从材料的感受力出发的:先感知材料带给我的情绪,再顺势塑造出它的形象。
Q:所以并不是刻意要去“做一朵蘑菇”?
A:对,我不会提前预设“今天必须完成某个特定形态的蘑菇”。每一朵蘑菇都像从指尖自然蹦出来的,没有刻意设计的痕迹。这种自然发生的状态,我觉得反而是作品最特殊、最吸引人的地方。
Q:蘑菇的造型——菌盖和菌柄的结构,在选择材质和形象时有什么特别的考虑?
A:最早我主要研究皮料。有一次处理菌盖部分时,突然发现皮料的质感与菌体的形态非常契合,于是顺其自然地尝试做成蘑菇的样子。每个材料本身的状态不同,最终呈现的蘑菇形态也会不一样。后来出现大型蘑菇,是因为它对我而言代表一种“坚定的力量”。我曾经是个容易摇摆的人,但这几年通过不断向内探索,逐渐感觉自己“扎根”了——像蘑菇一样与万物连接,创作时也变得毫无障碍。
Q:你如何判断一朵蘑菇是否“好看”?
A:关键在于质感和状态的饱满度。比如皮料表面的龟裂、面料的肌理、曲线的微妙变化……我从不刻意做笔直的、童话里那种标准蘑菇。每一朵蘑菇都有自己的姿态和情绪,像人一样独特。我用植物染色,以接近自然的方式处理它们,过程中常会收获意想不到的惊喜。
Q:你生活在杭州,这座城市对你的创作有怎样的影响?
A:杭州给了我很多养分。它既有文化底蕴和艺术氛围,又有可快可慢的节奏。我后来搬到杭州周边,更注重与自己相处——挖掘内在力量,而不是向外索取。这里的自然覆盖率很高,能让人停下来感受周围的事物,这种环境特别适合创作。
Q:为什么对布料这类材质如此钟情?
A:材质对我来说是有“语境”的。比如有些材质温润中带着坚硬,有些柔和光滑,有些是棉质的柔软……每种材质对应着不同的词汇和情绪。我大量使用基础棉质进行植物染色,再通过褶皱、肌理等手法赋予它们不同的韵律——就像用同一个词汇写出不同的句子。
Q:这种对布料的亲近感是否与个人记忆有关?
A:是的。我最早的记忆是被哥哥放进衣柜,一开始是黑暗和恐惧,但很快闻到妈妈衣服的味道,用脸蹭那些衣物时,感受到一种温暖的抚慰。后来在我人生低谷时,也是这种材质给了我安慰,缓解了内心的焦虑。它像母亲的拥抱,那种力量很难用语言描述,但会自然流淌到作品里。
Q:作为女性艺术家,你如何看待性别与创作的关系?
A:女性艺术家的情感可能更细腻,视角更微观。我的创作常从细微处切入,而男性艺术家可能更偏向宏大的叙事。但这种差异不是绝对的,只是个人感受的延伸。
Q:这次展览空间与作品的结合有哪些特别设计?
A:这个空间仿佛是为蘑菇准备的。清晨的光从院子斜射进来,打在蘑菇上,那种灵动感就像它们在自然中生长。我们调整过布局——把大蘑菇放在光影交错的角落,让“根”的作品处于较暗处,象征它在大地中生根。一切追求恰到好处的自然美感,甚至门口树下的那组蘑菇也像是自己长出来的。
Q:未来的创作会继续围绕蘑菇吗?
A:我不设上限。一旦设限,反而会失去惊喜。或许会尝试让蘑菇与金属和工业等元素碰撞,看看能产生怎样的火花。保持开放,创作才会更好玩。
荆禧
你必须马上使用自己

“荆禧个展:你必须马上使用自己”在art feel空间开幕。荆禧是一个生于2000年的年轻艺术家,在展览中,视觉最强烈的作品是她在一片红土的山上挖出一阶一阶的梯子,然后人缓缓地沿着梯子向上爬,再跌倒,那部作品的名字叫作“下一个登山者”;而作品“船掌”则是她在冰冷刺骨的湖里面行走,手里捧着一条金鱼……

荆禧
生于北京,曾就读于伦敦艺术大学切尔西艺术学院,现工作、生活于北京。“许多年前一位朋友告诉我,艺术家要像野草一样生长,烧不尽,吹又生。那时,我们正在秋天下午的房间里做雕塑。室温未经察觉地下降着,两个人用发冷的双手搓着油泥,使它变得更柔软一些。枯荣交替,野草总是蛮横地长着,因为一些原因被剿除,随后又茂盛起来……”
荆禧这样讲述她心中的艺术,身体是她最熟悉、最有力量、最能够表达自己的材料。
“在作品中,每一具身体都被当作了材料来使用(包括刚刚你滑动的那一下)。多数时候,艺术家在提前设置好的指令和行动环境中使用自己。这是目前我正在探索的一种方法。在常规印象中,行为艺术总是激烈的,这是它的另一种魅力。我个人想试着温和一点。”
这样的表达,好似一个历尽千帆的中年人。
“你看地上洒的水的形状像小狗骑自行车,每只蜗牛的纹理其实都不太一样……”谈及灵感来源的时候,她轻盈的语调又迎来转折,这不是“小王子”嘛。
人生的价值和意义都是通过实际生活中的行动创造出来的!
对话荆禧
Q:看你的作品,会想到2000年初的观念艺术家,作品又猛又洒脱。
A:我感觉我的呈现形式还是蛮温和的,可能在内容上会给人一种这样的感觉。我在看《荣荣的东村》那本书时,里面讲“那时的他们穷得只剩下自己的身体”,这句话蛮打动我。我在行为之前其实尝试了很多形式,探索到最后也是“只剩下了身体”。身体是很即时的,无论是生成的即时性还是表达的即时性。它对我而言比较熟悉。
Q:展览名“你必须马上使用自己”代表什么?
A:这句话也是看完“东村”那本书之后写的,当时写了一篇比较抽象的散文,我从里面摘取了这句话作为展览的题目。原句是“你必须马上使用自己,因为不去使用就会立刻失去”。我大部分作品都在积极地使用自己作为材料。肉身不是一个恒常存在的东西,它每天都在缓慢地变化。能够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使用它去作表达是很幸运的事情。我现在回看,甚至连一年前做的作品今后都很难再去做了,无论是想法的转变还是身体的状况,它们都是作品形成的条件,这样的条件总是阶段性地存在。我常有一种时不我待的感觉,所以在有条件的时候最好马上行动。
Q:你们这代人选择很多,受过良好教育,能用各种媒介表达。为什么选择行为艺术?
A:可能只是看起来选择多。人最终都会滑向自己想做的事,包括做艺术也是,我们做创作也是因为好像只能做创作。这是一个自然过程。另外我也试图用这种方式让作品中的“人”的社会属性弱一些,材料的成分多一些。
Q:现在的年轻艺术家更轻盈聪明,但你的作品仍能看到疼痛。
A:在土里的时候还是很舒服的,虽然手确实是受伤了。但是做任何事都要付出点代价,这个还是能承受的。不过我在表达的时候并不侧重于疼痛,我还是想多说一点别的事情。人是时代的产物,我总觉得三十年前是一个把人往出放的时代,虽然是很荒蛮的,就像曾经的东村是现在的朝阳公园一带,我得知这一点的时候还是很震惊的。荒蛮之中总是存在许多可能性,所以那时候的作品也会带着强烈的野性气质,风险和机遇总是共存;现在时代好像又在把人往里收,一切都越来越明确,人们倾向于寻求一种安全和稳定,因此可能也没那么疼痛了。
Q:性别对你来说是负担、武器,还是基础条件?
A:性别是我的出厂设置。我需要承受每个女性都要承受的痛苦,这是一件改变不了的事情。不过创作时我不太考虑女性这个身份。阿布拉莫维奇也是女性艺术家,但我喜欢她并不是因为她的性别,而是因为她的斗志和勇气。做行为艺术是需要勇气的。这种精神并不依托于性别存在。
Q:你怎么看作品中的“看与被看”?
A:作品被观看时,“懂”从不是唯一的价值,创作者为了观照精神而作,而观看者则是为了寻求激发而看,本质都是在各自路径上的探索。作和看的不协同,往往才体现着被表达之物自由,误解也是很好的误解,它使创作的权利不断绵延。我反对用艺术作品区隔阶级或是挑选观众,创作应当是为了能让人们彼此有机会连接在一起,这样我们就不会那么孤独。
Q:作品的灵感从哪来?
A:它是一个直觉性的东西,不需要刻意去找,会在日常中自动出现。我的灵感时常是一个图像,一般要等实践完成之后我才能真正理解自己想表达什么。另外我一直希望呈现一种简单的语言,让每一个人看了都能多少有些感受,或是短暂地被“打破”。为所有人创作这件事,虽然可能永远都无法实现,但我还是愿意为此努力,哪怕多触动一个人都好。
Q:把轮椅改成自行车这类转化,灵感怎么来的?
A:它会自己生成。当有图像出现的时候,说明潜意识里有无法用语言表达的东西,这也是必须要做作品的原因。我很反感在一个极其抽象的作品旁放一篇不知所云的哲学解释,我觉得这是在主动地创造隔阂。
Q:什么样的人吸引你?你对年轻人感兴趣吗?
A:我不认为年轻人是一个群体,年轻可能是他们唯一的共性。我个人的经验上,一个是感觉年轻人之间分化也很大,什么样的人都有,很不好只用一个“年轻人”去定位;另外我又不感觉年轻人和年纪大的人有什么太大的区别,可能这个区别还没有“宁要痛苦不要麻木”和“宁要麻木不要痛苦”的人之间大。我从十几岁开始就和二三十岁的朋友一起玩,现在的朋友也是什么年龄阶段的都有。我觉得人们能相遇并且产生一些关系是很稀罕的事情,这件事情要看机缘。
Q:女性创作者的环境如何?
A:可能我并不处在所谓的“环境”里,我没有太切身的感受,一直都在遥远地旁观。并且困难都是个性化的,什么性别都需要面对自己的问题。
Q:《寒川一梦》这个作品,是你在冰上种树,这是包含对生命力的思考吗?
A:更多是对生命本身的思考,你全部的人生在恒常的变迁当中是很暂时的。冰面是暂时的陆地、树是暂时的生命,甚至种树的人也是暂时的人。死亡是所有人的结局,我很恐惧这件事,这种恐惧促成了这个表达。
Q:创作时会经历强烈的情绪波动吗?
A:灵感生成阶段会比较容易经历这些。实践的时候其实更倾向于机械地做事情,不太会有什么特别的情绪。我总是在实践中面对非常实际的问题,心情和大部分人没有什么区别。焦虑就焦虑地做,害怕就害怕地做,事情总得往前推。还有一种情绪,我称之为“开心到崩溃”,比如这次做展览,每天都很疲惫,但我知道这是好事。这是一种好的崩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