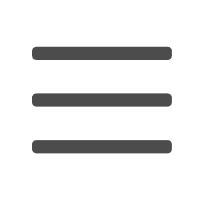编辑 王雅静 文 韩文苑 人物摄影 李英武 美编 崔洪洋

赵冬梅的研究室在李兆基人文学苑5号楼,开门可见一面巨大、明亮的窗。两年前的秋天,她搬进这间新办公室,那时,窗外还是棕灰的树干和枯黄的叶,赵冬梅立刻爱上这面风景,她称自己为“一窗秋色主人”。她在这里读书、撰稿、改论文、录教程,解答学生的疑问,也听取他们的心事。现在,夏天到了,她手边是古籍、专著砌成的书墙,抬头是磅礴的翠绿,有学生为她刻了一方印,印上正是:“一窗秋色主人”。
在宋代历史这个领域,赵冬梅是进行过深入研究、讲解也最受人欢迎的学者之一。在中国持续两千多年的帝制时期里,王朝与王朝间在政治和制度上几乎是同构的,也就是说,深度解剖其中一个朝代,就有可能把“帝制”给看个清楚。赵冬梅希望透过北宋,解密中国帝制时期的政治文化。
像许多人一样,赵冬梅对历史的兴趣,来自于对过去的人的关怀,对今天人为何如此的好奇,以及对未来人类命运走向的关心。她的研究,即把帝制中国视作一种国家类型,细看它的治理与兴衰。
对制度最初的敏感来自她切身的体验。1971年,赵冬梅出生在河北唐山,1976年唐山大地震后,母亲带着她和妹妹坐了三天火车,投奔当兵的父亲。那一年,赵冬梅该上小学了,却没有户口。好心的班主任接收了她,却无法改变她随时可能失学的处境。这样的事,成年后也发生过。她曾在又渴又饿时经过了北京一家国营粮店卖熟食的门市部,但口袋里的100多块钱毫无用处,因为没有粮票,她只能对着花卷干瞪眼。这是她注意到制度与制度中的人的困境的开始。
宋史学者眼中,宋被分成北宋、南宋两个阶段,北宋不仅拥有比南宋更完整的政治历程,北宋中期还曾出现过帝制时期儒家政治的最好成绩——不杀士大夫,因而孕育了一代不同政见人才的“宽容政治”。“这个最好成绩怎样出现的,以及这个最好成绩是怎样落幕的,它为什么没能延续下去?我要解释的就是这个。”她从北宋5个代际中选取了几位代表人物,比如寇准、司马光,打算用这些政治家命运的沉浮,呈现北宋政治文化的兴衰变迁。
“其实,所有历史中的人都是盲目的,就像所有今天的人也是盲目的一样。我们根据自己非常有限的信息,做出我们自己认为是对的的那个判断,对方也是这样。行为彼此碰撞,最终就是你没有实现你的想法,我也没有实现我的想法,我认为,这就是历史最大的复杂性。”好比王安石与司马光,两位最一流的、深爱着宋朝的理想主义者,他们的合力却将这个国家最美好的政治推向毁灭。与此同时,历史又是如此随机。就像张方平才是宋神宗最初选定的改革人选,结果偏偏在他最接近权力时,他的父亲去世了,张方平只能回家守孝,只得另寻人才的神宗,这才留意到王安石,才造成了王安石与司马光的互动、恩怨与纠葛。“其实历史学者能够做的,就是通过我们的研究和思考,给大家多提供一点走进这个复杂性的细节。”她说。
53岁的赵冬梅,身上依然有一种天真,和一种树一样苍翠的生机。她非常相信纯粹的人和人之间的情感,她坚持人应该帮助人,对他人——学生、朋友、困惑的读者,或是观念并不一致的学生家长,她都有极度的耐烦。这种善意,是她翻遍了古书,承认了政治之残酷与人性之复杂后的主动选择。最直接的体现是,在书里,她批评阴暗与保守,又对这些人抱有充分的同情。因为对制度史的研究,让她清楚看见过人的困境。
对赵冬梅来说,认识生活、认识自己与认识历史同样重要。时间在她身上留下痕迹,比如她渐渐掺白的头发。《宽容与执拗——迂夫司马光和北宋政治》新书分享会上,一位读者说,还是习惯您之前黑发的样子,赵冬梅笑了笑,“我倒是更习惯现在的我。”她用她一贯确信的语气说。
雨停之后,赵冬梅带我们在学校里散步,在中文系一个使用率并不高,因而总被她借来散步的小花园里,这里有粉色绣球花,紫藤,和就要开花的枣树,雨后树叶变得透亮。“北大有600多种植物,200多种鸟。”她轻轻地说。
现在的赵冬梅,是研究宋史的学者,是一个孩子的母亲和一个家庭的女儿,是许多学生的老师和许多网友的同好,是一窗秋色的主人,她品饮春茶,欣赏朋友烧的瓷,尽量理解儿子的追求与选择。生活滋味漫长,就像她春荣秋枯的窗框。赵冬梅说,意义无需向外求,欣赏自己的日常生活,就是握住生活主动权的开始。

赵冬梅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宋史研究会理事,活跃在多种媒体的严肃历史知识传播者。曾任英国牛津大学圣安东尼学院访问学者,德国维尔茨堡大学汉学系、法国巴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香港教育大学访问教授。致力于宋代制度、政治文化和历史人物传记的研究、写作与传播。著有:《宽容与执拗:迂夫司马光和北宋政治》《法度与人心:帝制时期人与制度的互动》《人间烟火:掩埋在历史里的日常与人生》《大宋之变,1063—1086》《文武之间:北宋武选官研究》《武道彷徨:中国古代的武举与武学》《千秋是非话寇准》;译著有《天潢贵胄:宋代宗室史》《中国转向内在:两宋之际的文化内向》等。

《宽容与执拗:迂夫司马光和北宋政治》
作者:赵冬梅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出品方:见识城邦
本书以北宋著名史学家、政治家、一代大儒司马光的成长轨迹、人生经历、社会活动为核心,讲述了其生命所跨越的自真宗、仁宗、英宗、神宗至哲宗这五个朝代的历史变迁,以及与其休戚相关的北宋政坛上如王安石、范仲淹、欧阳修、包拯、苏轼兄弟等巨星们的互动、恩怨与纠葛。北京大学宋史专家赵冬梅教授以多年宋史研究积淀为依托,自司马光的家世渊源追溯而起,将其初入仕途至崭露头角,再至成为股肱之臣,乃至走上宰相高位进而影响宋代历史走向的人生经历进行了细致讲述。其间,既有对司马光与恩师庞籍、挚友庞之道深厚的师友之谊的描写,又有对其在激烈变革的大时代下与各方势力间思想交锋、政治角逐的讲述,乃至对司马光怡然自得的著述生涯和其思想、德行、为人处世的立场进行的生动刻画。


对话赵冬梅:
Q:不管什么时候、在什么场合见到您,我都能感受到您身上的热情和认真,即便是在做喜欢的工作,您从来没有产生过倦怠感吗?
A:我从1998年开始工作,到今年已经有26年,时间是够长的了,而倦怠感,老实说好像真的没有,因为当年我选择工作时已经把倦怠感考虑在内了。比如我那时也考虑过要做公务员,可是后来又想,自己是受不住日复一日的重复性工作所带来的磨损的,就放弃了。而我现在从事的工作,不管是研究还是教书,所面对的人是新的,教的内容也是不断变化的,这些年我没有做过一件重复性的工作,包括研究,其实是可以用一个模式去完成100篇论文的,但是我发表个一两篇之后就会觉得够了,我不要再这样做这个题,我要换一种方式完成。
我现在正在进行的人物传记写作的工作,加起来希望可以构成一份对北宋政治文化史的叙述。每天,我接触到的研究对象不同、参考材料不同,它们所带出的我对于我所处时代的感受和我内心的感受也都不同。或许我也曾有过一瞬的倦怠闪现?但是从总体上讲,我对我的工作、我的校园、我的生活,都是时时期待的。当然我属于是特别幸运的人了,选了自己喜欢的路,确实是把兴趣爱好跟生命、生活结合在一起了。
Q:关于研究对象带给您的对时代、对内心的呼应与感受,能不能做出更具体的解释?
A:常识是,所有人都是在自己的代际规定之中讨生活。那我用苏轼举例。苏轼的代际背景就是等他开始要大展宏图的时候,其实可作为的空间已经不大了。当时所有人都要选边站,他不愿意选,因此也就注定了他不会太如意。苏东坡作为一个儒家的士大夫,修身齐家没有问题,可是治国平天下就没有机会了,那这时候他当如何自处?
关于“是意义支撑起了我们的生命”的说法,我也同意,可是有时候,有些事你就是做不成的,你可以改变那个小的环境,但你无法超越大的时代,无法跳出你的代际存在。时代跟人一样需要时间,对时代中那些不好的东西,时代本身也需要用时间来抵挡、来慢慢度过那个周期,可你就是赶上了这样的时候,你要怎么办?如果这时苏轼仍然抱持着原有的意义不放,把治国平天下作为他生命最主要的抱负,那么他就永远不会快乐了,但是苏轼退回来了,他在政治上决不站队、决不妥协,在弹琴、造墨、写书法、写诗词这些还允许他做的事情上,他都做得很快乐。而且他依然有爱,爱国家,爱人民、爱朋友、爱妻子、爱同事,被贬谪了却依然惜才。所以生命的意义是要不断调整的,不是说你被赋予了一个意义而后就固定了,生命的意义要在生命中寻找,每一天,我们都在寻找自己。其实生命的意义不是向外求的,其实“我”就是意义,“我”就是价值,承认自己的日常是有意义的,就能过得很开心。
Q:您非常欣赏的司马光和苏轼,会在某些时刻成为您做选择时的参考或者榜样吗?
A:其实不会有特别具体的指导场景,像小学写作文时说的那种我灵光一现、想起了雷锋于是就做了什么的事是不会发生的,但是我们读过的书、看过的人,尤其在我们与他们密切接触过之后,他们的品德就会被你默化于心,比如司马光的诚,比如苏轼的坚持、有趣,任何时候都不会放弃生命,任何时候也都在赞美生命。还有照顾他人,离得近了,看得久了,不知不觉中,你也会对自己有更高的要求。
Q:您一直把司马光当做“偶像”,不过新书里,仍然还是写明了他这个人的局限性,甚至写进了新书的标题里。
A:司马光是我的研究对象,我也非常尊重他诚实的品质,和他对于宽容政治的尊重与追求,可是我们也必须看到他的无能和无力,因为这也是真实的。真实很复杂,同时包括好与不好,但真实本身就是美的,这不是那种抽象的美。人具有多面性,现实中的人是,历史上的人也是,没必要把一个人变成干巴巴的仅保留某一面的偶像。
Q:您做过电视节目、播客节目,您的书和研究受到学界和读者们的喜爱,也获得了相当多的社会荣誉。目前为止,您自己最喜欢的、您觉得最能代表您的作品是什么呢?
A:哎呀,我想我的答案其实首先是我的儿子,因为他向我展示了生命顽强的力量,他拥有我所不拥有的勇气,比如在意识到现有的教育体制与自己的追求并不契合之后,他选择了抗拒,与体制化的教育(暂时)说了再见,但在这种状态之下,他依然完成了很好的社会性的发育。他勤奋、能吃苦,动手能力很强,有创造力,我还是要给他高度的赞美,拥有这样的孩子,我确实是很得意的。
我自己的书里,我觉得《宽容与执拗——迂夫司马光和北宋政治》《大宋之变:1063—1086》《文武之间:北宋武选官研究》都写得很好。我对自己的文字是很自豪的,我觉得它们基本做到了流畅,在这之上,还能带给人一点美的感觉。
Q:您有喜欢的作者吗?
A:最喜欢的是汪曾祺。我觉得沈从文推开了我的一扇窗,但我感觉自己在精神气质上与汪曾祺最是心灵相通。年轻的时候有一次汪先生来北大讲座,当时受了钱钟书先生的影响,就是那句“你吃了个鸡蛋,觉得不错,何必要认识那下蛋的母鸡呢?”为了保持汪先生在我心中的神圣感故意没去见他,其实当时我就在附近的教室里看书,现在觉得当时自己太傻了。除了汪曾祺和沈从文,年轻人里我还喜欢李娟,我喜欢她那种含着生活的痛的文字。写散文是要有生活的,是不管生活如何沉重,你都能够存活下来,能幸免于难,并且你的写作不是要给苦难镀金边,而是就只是告诉命运,你不屈服。我很欣赏这样的人。我觉得人的伟大,不在于什么丰功伟绩,能够自食其力、过自己满意的生活,并能赞美自己的生活就足够了,我认为人最失败的就是讨厌或者不承认自己的生活。
Q:任何一点都好,给今天的年轻人一点建议?
A:我希望每个成年的朋友都可以把自己承担起来,不要把目光集中在别人身上,而是尽量思考和行动,自己怎么让自己快乐。我在线下活动时常被年轻人问到的问题就是你有没有遇到什么挫折,怎么可能没遇到过挫折呢?但是挫折是可以过去的。
Q:最近这段时间,生活是否发生了什么不同?
A:有个进步,是我发觉自己好像可以更孤独却更快乐地活着,起因是某一天我发现自己好像不用去倾诉了,当然这不是绝对的,比如咱俩目前的对话也是一种倾诉,写日记、发微博或是解答学生提问时其实也是倾诉。我只是想说,倾诉可能是一种定格,有些话当你说出来,你的情绪就被固定成那样了,有时别人倾诉你之后又给你他们的反馈,那这个情绪又被强化了。其实这时,你的情绪可能是被夸大的,可能是你原本自己待一会儿就度过去了的小事儿,可一旦讲出口,它就可能真的变成一件“事儿”。当然也因为人生在世,得知己二三已是幸事,所以我们首先要自己强大,要爱自己,而不要嫌弃自己。当然我年龄大了,年轻的朋友要做到这点可能不容易,但总体上,在道理上或者倾向上,我想是这样的。
Q:看您的作品、您的观察,感觉历史学家对于“随机性”与“周期”都有着深刻的认知,这或许是现在大家特别希望寻求的经验。
A:作为一个小的历史学者,我老老实实地说,我在学历史的过程中,看到最多的就是偶然性对个体、对社会的巨大影响,偶然的影响力要远超所谓的必然。一定要接纳偶然,因为历史本身就是偶然间碰出来的。
至于周期,我觉得时代高涨的时候你不要轻飘飘,时代低迷的时候你也不要就此沉下去,扎扎实实做自己就行了。我现在总是嘱咐我的学生,疲惫与焦虑的时候,先想想自己是不是觉没有睡足,睡醒了再起来解决问题。
Q:如果世界如此随机,那么做决定时,考虑什么最重要?
A:我觉得跟随你此刻的本心可能比较重要,因为常常是你算来算去想了很多,但你做出的这个决定其实并不能直接指向那个结果。
Q:人的时间是有限的,给了别人,留给自己的就一定少了。我想起邓小南老师,在70多岁时,主动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组织活动和人才的培养上,帮年轻人锚定方向,建构他们自己的研究体系。其实她也可以去继续自己的研究,可她觉得,相比自己论文十年期的进展,不如用那个时间来培养下一代。我从您身上也一直能感受到这种奉献感,这是一种做老师的本能吗?
A:所以出租车司机们猜我职业的时候从没猜错过。帮助别人是北大历史系一个相当重要的课题。个体的生命是很有限的,但我们都在历史的长河中,在某个传承的谱系中。邓小南老师的父亲是当代宋史研究的开创者、奠基人邓广铭教授,邓老师的同辈有张希清老师,他们后面是我们这一辈,我后面还有更年轻的我的学生们……要看到这条河流的生生不息和流动,要知道我们每个人除了个人的价值,还都有共同的事业——是的,某种程度上我认为可以用到“事业”这个词。每年清明节,我们都要去给邓先生扫墓,现在那个队伍已经非常壮大了,年年都去看先生,这就是北大宋史研究一次次的展示与宣誓,因为人一定要有理想,但人的理想很可能会超越自己的生命。同时我确实也觉得,人需要有一点奉献精神。
Q:您觉得读史最有意思的是什么?
A:那是真实的过去,而真实本身既是有趣的,也是有力量的。虚构其实是在尽可能地模拟真实,但它永远不如真实有趣,因为虚构一定会遵循某种逻辑,可是真实发生的不需要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