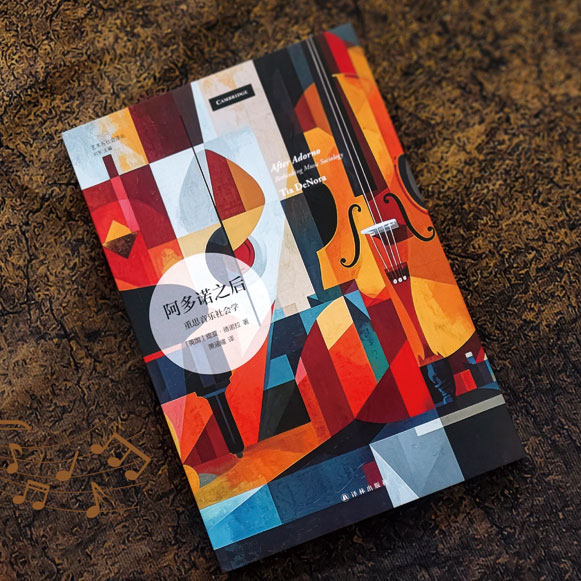西奥多·阿多诺的深度思考 重构社会学与音乐学之双向通道
时间:2025-10-09 18:37 来源:北京青年周刊
编辑 王雅静 撰文 王雅静 资料提供 译林出版社设计 聂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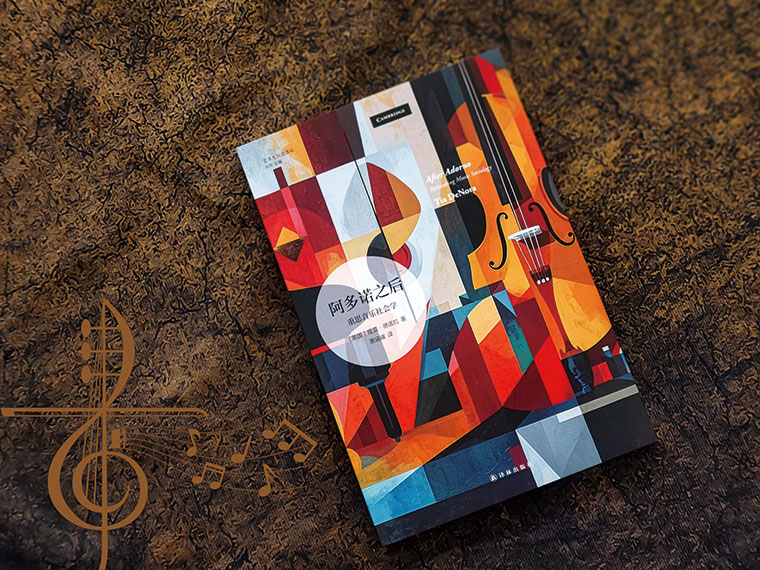

西奥多·阿多诺
西奥多·阿多诺是人类20世纪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在德国近现代思想史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他认为音乐能够影响人们的意识,是一种社会管理和控制的手段。如果说阿多诺为社会学与音乐学的跨学科融合开辟了道路,那么,本书的作者提亚·德诺拉则将这一学术传统推向了新的高度。她通过研究证明,社会学与音乐学的对话至今仍是一条双向通道。以下文字摘自本书。

Tips:《阿多诺之后:重思音乐社会学》
本书作者提亚·德诺拉从阿多诺将音乐视为社会生活动态媒介的研究视角出发,极大地丰富音乐社会学理论。德诺拉从认知维度、情感维度以及音乐作为管理工具的角度展开了深入探讨,并开创性地提出了辅助理解音乐社会学的框架,认为重思阿多诺不仅可以更新对音乐结构、倾听模式的理解,更能超越阿多诺起初的研究方法和理论水平。
西奥多·阿多诺
德国著名哲学家、美学家、社会学家。生于法兰克福一犹太酒商家庭,卒于瑞士菲斯普。1921年入法兰克福大学攻读哲学、心理学和音乐,1924年以论文《胡塞尔现象学对物体与意识的超越》获博士学位。法兰克福学派第一代的主要代表人物,社会批判理论的理论奠基者。阿多诺深谙现代音乐,博士毕业后曾赴维也纳跟随勋伯格小组学习作曲。他的音乐批判理论是法兰克福学派社会批判理论中最具特色的。
提亚·德诺拉
英国国家学术院院士,埃克塞特大学社会学与哲学系音乐社会学教授。代表作有《贝多芬与天才的建构》《阿多诺之后》《音乐避难所》《日常生活中的音乐》等。
音乐很重要
不少人都认为音乐拥有某种力量——它可以跨越文化和时间,与教诲、疗愈、腐蚀这些变革性的事件联系密切。这种想法认为音乐会作用于意识、身体和情感,所以要对音乐严加监管和控制。
西方音乐史上不时会出现褒扬或斥责音乐的力量,在涉及与歌词、剧本有别的调性时尤为有趣。这种现象在宗教音乐中极为常见——查理大帝(Charlemagne)曾“改革”圣歌,教皇格里高利十三世(Pope GregoryⅩⅢ)呼吁“修改、清理、纠正和翻新”教会音乐(Hoppin 1978:50),16世纪末新教摒弃精致的复调而倡导简洁的赞美诗颂唱,巴赫(J.S.Bach)认为宗教音乐的目的就是“组织信众”。而在政治领域,音乐常因其影响而被利用或被压抑。德米特里·肖斯塔科维奇(Dmitri Shostakovich)曾奉命创作纪念俄国革命的交响乐,后来又因创作“颓废”音乐而遭到谴责;纳粹德国下令驱逐无调性音乐(atonal music);近来还有因演唱国歌而引发的轩然大波——性手枪乐队(Sex Pistols)的《上帝拯救女王》(God Save the Queen)、吉米·亨德里克斯(Jimi Hendrix)的《星条旗之歌》(Star Spangled Banner)。这些观点都认为音乐会煽动或颠覆共识。若将视野放至全球,戏剧性的例子则更多,最近有西方媒体报道称阿富汗几乎禁止了所有形式的音乐。全世界都认为音乐会激发某些东西,比如:恐惧。
关于音乐、道德和教育的辩论如今在学界内外依旧激烈——比如,所谓“莫扎特效应”害怕重金属戕害年轻人、对一切可能带来破坏性影响的音乐风格忧心忡忡,甚至有学者在研究音乐如何危害驾驶安全。尽管音乐有时不过是替罪羊,有时则是批评听众及其文化的靶子,但忽视音乐自身(music’s musical)的力量显然十分草率。音乐会发挥作用仍是大部分人的常识,大家深谙此点是因为都曾有体会,因此我们有时会诉诸音乐,有时则避之不及。总之,所有人都知道音乐很重要。
关注音乐力量一直是社会理论中的一种传统,最迟也可追溯到柏拉图。苏格拉底在《理想国》(The Republic)中称“:我们的护卫者看来必须就在这里——在音乐里——布防设哨……因此,如果从一开始做游戏起就能借助音乐养成遵守法律的精神……(”1966:72)这部名著相当清晰:审美、仪式与道德秩序塑造了社会秩序,但仪式与艺术自身同时也见证了这些秩序,最终,两者难以分离。这类对社会秩序基础进行概念化的做法在19世纪依旧盛行,这在后来涂尔干(E.Durkheim)对基本形式的强调中可被找到——尽管该作品忽视了音乐的作用(Durkheim 1915)。
随着机械复制技术、广播媒体和娱乐产业的发展,人们也许想当然地认为讨论音乐社会功能的需求会与日俱增。可其实在圣西门(Claude Henri de Rouvroy)之后的社会哲学中,音乐的重要性反而被削弱了。等到20世纪社会学家和社会理论家转向音乐时,他们甚少提及音乐的社会力量。相反音乐更遥远了,它是“反映”社会结构的媒介,无论以哪种方式,它与社会结构总是平行的。这种形式主义范式也是韦伯(M.Weber)、狄尔泰(W.Dilthey)、齐美尔(G.Simmel)和索罗金(Pitirim A.Sorokin)等理论家的特点,这极大地阻碍了学者去关注音乐与道德行为之间的联系。这种中立立场引发了一个问题,即社会—音乐研究从关注音乐“造成了”什么后果转向关注是什么东西造就了音乐。与此同时,音乐社会学(music sociology)开始转变为音乐的社会学(the music of sociology),措辞上的细微差别意味着有关音乐和社会最有意思的问题已被剔除,准确来说,就是社会中的音乐和作为社会一部分的音乐被剔除了。即便是在20世纪80年代末的“艺术界(”art worlds)、20世纪90年代的“文化生产(”production of culture)这些卓有成效、脚踏实地的聚焦中,也从未讨论过音乐的影响问题(Peterson 1978,Becker 1982,DeNora 1995)。
这样一来,音乐的社会学暗中贬低了音乐媒介;音乐从某种活性成分沦为有待阐释的对象,从生机勃勃的力量(force)沦为死气沉沉的产品(product)。音乐的降格使其在20世纪变成一个学术且专业的话题,人们对此感到无聊乏味、激情不再,以至如今,在普遍又日常的音乐感受与专业且精深的专业描述之间存在的鸿沟似乎变得正常和可以接受。但近年来似乎有所变化,跨学科研究已在很大程度上纠正了音乐,因为音乐实际上是“行动中(”in action)的音乐。不过,前路依旧迢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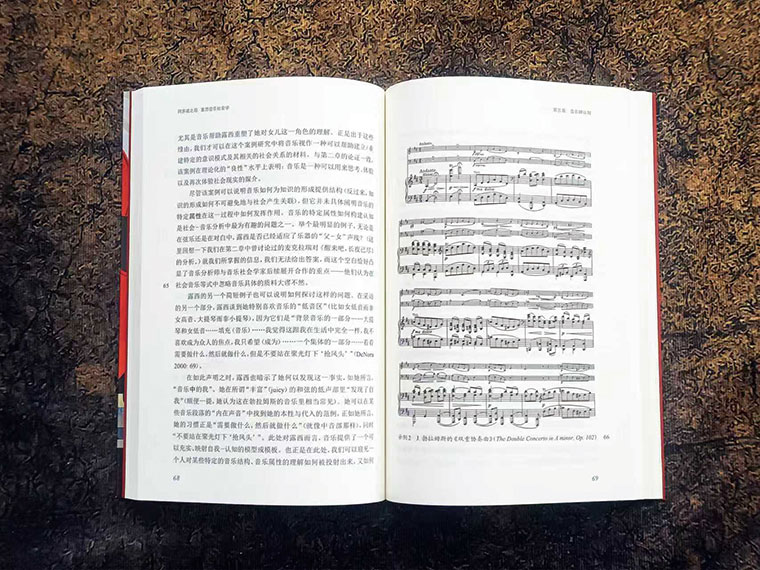
进入阿多诺
正基于此,我们方能理解阿多诺及其社会—音乐研究的独特之处。无论出于何种原因——他的作曲家身份、在世界各地与各种文化间流亡迁徙的经历,还是同其他批评理论家的关系——阿多诺都要比20世纪上半叶任何学者都更适合开展这项工作:将音乐力量理论化。因此,即便阿多诺的研究及方法存在诸多错误,但他后来仍被尊为音乐社会学之父(Shepherd 2001:605)。
阿多诺相当熟悉音乐,在他看来音乐并不抽象,因此不能从塑造音乐的社会力量或音乐本身的结构属性来理解音乐;相反,音乐是某种鲜活生动的媒介。阿多诺基于此开启了他的哲学和社会学研究。如后文所言,阿多诺用音乐来思考(to think with)。他致力于探讨音乐如何改变意识(无论好坏)。重点在于,他的社会—音乐研究提供了一个关键视角,而这个视角涵盖甚广——知识哲学、知识社会学、意识的文化史,以及社会凝聚、支配、服从的历史等。所以如果要理解阿多诺的音乐研究,那就必须将其置于更广泛的关切之中。